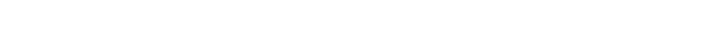一、从小一开始的“军备竞赛”
对44岁的保险公司精算师李哈里先生(Mr Harry Lee)而言,儿子加布里埃尔(Gabriel)在2022年进入小学一年级时,仿佛就是一场教育“军备竞赛”的开端。加布里埃尔属于“SG50宝宝”——2015年新加坡庆祝建国50周年时出生的一代。那一年的出生婴儿超过3.7万人,是2015年至2024年间记录到的最高数字,这也可能意味着学额竞争更为激烈。小一注册分为多个阶段,较早阶段优先考虑校内有兄姐就读或父母为校友的孩子;这些条件加布里埃尔都不符合,因此李先生把目标锁定在2B阶段,也就是父母曾在学校担任义工的家庭可享有优先权。他们希望进入居住地后港的一所热门学校,看中其学术口碑与价值观教育。李先生回忆:“我们每天做交通义务指挥的值勤,每次45分钟,累计到40小时,一周去一次,持续40周。”按规定,家长义工必须完成至少40小时服务才会被纳入2B阶段考虑,但学校并不会保证一定有名额,“他们也强调并不确定”。“那一年对我们来说压力非常大。”他说,任何教育体系都会存在竞争,但许多焦虑来自不确定性;若能提供更清晰的入学指标数量而不仅依赖历史数据,将更有助家长评估孩子的入学概率。
二、“军备竞赛”贯穿各个关键节点
受访家长形容,陪孩子走过校园生活就像在跑一场无法退出的赛跑:有人提早多年规划教育路线,有人投入补习与才艺课程,试图在热门学校竞争中占得先机。学生也反映,他们承受考试与期待的压力,有些人甚至觉得自我价值与成绩或就读学校紧密相连。政治领袖已多次回应相关问题:在9月的总统致辞辩论中,总理黄循财(Lawrence Wong)表示政府将在新任期进一步降低“一考定终身”的影响,并推动新加坡从以分数为唯一标准的狭义精英主义,迈向更广泛、更包容的评价体系;他也提到,教育曾是他那一代的“社会平衡器”,未来家长与孩子不应把教育视为负担,而应视作跳板。同场讲话中,教育部长李智陞(Desmond Lee)表示新加坡必须摆脱把教育当作“军备竞赛”的心态,教育部将研究如何降低考试的高风险属性,更聚焦学校生活中的非学术面向,并防止资源更充足的家庭过度“催熟式”培育孩子。然而在许多家庭看来,竞赛仍是日常现实:首个重大关卡是小六会考(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,PSLE),它决定孩子可以进入哪些类型与范围的中学。三名孩子的母亲、47岁的传播顾问乔蒂·汗(Jyoti Khan)说,体系压力“几乎会传染”,当孩子们逐步走到PSLE,她发现自己也被卷入大部分家庭的节奏:补习、规划全年围绕考试运转;“每个家长都在谈今年是不是‘大考年’,你会发现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加入那种讨论。”她努力不把焦虑传递给分别就读中四、中二与小二的孩子,但当儿子尝试通过直接收生(Direct School Admission, DSA)申请中学时,她仍投入其中,帮助他打磨吉他曲目与个人陈述。
三、“好学校”供不应求,层级感仍在
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副教授蔡文森(Vincent Chua)指出,竞争持续存在的根源在于“好学校”的需求超过供给:即便新的PSLE计分制度旨在降低竞争性,学校分布在现实中仍呈现某种“曲线结构”:少数精英学校、多数被认为不错的学校,以及少数较不受追捧的学校;他说:“只要这种层级存在,竞争就会持续;现在离理想状态中的每一所学校都被视为好学校仍有一段距离。”家长会觉得必须投入补习、才艺课程与持续监督,而考试也更难在高分段拉开差距;当教育变成竞赛,社会比较就会成为生活方式,最终形成升级的“军备竞赛”,带来压力、倦怠与青年福祉下降。汗女士也表示,人们仍会以就读学校来评判他人;不少人相信进入“好学校”不仅是品牌,更意味着社交与校友网络资源。随着孩子一路升学,这种压力往往在O、N、A水准等被视为通往高等教育的关口的关键考试时更为强烈,。
四、结构性不平等与“私人投入”推高竞赛
多年来,政府推出更多路径以降低对单一考试的依赖,并更全面地评价学生:教育部表示将持续优化DSA甄选流程,以确保学校把焦点放在学生发展、甄选更客观透明,并让DSA保持可及性;全面科目编班让学生可按科目选择不同难度层级;新的PSLE成就等级(AL1至AL8)自2021年实施;取消中小学年中考试也在推进,初级学院逐步跟进;近期初院入学计分方式由计六科改为计五科,希望学生有更多时间进行全人发展;2027年起也将以新的中学教育证书考试取代现行O、N水准考试,配合按科目层级评估的方向。但家长反映压力并未真正减轻。46岁的公务员黄珍妮特(Jeanette Wong)说,她的两个孩子在新旧计分制度下参加PSLE,压力程度都差不多:旧制度强调相对排名;新制度则可能让更多学生出现相同总分,导致更多学位需要通过抽签决定。自2023年以来,家长团体推动改革,提出包括检讨班级规模与资源配置、让PSLE变为可选等建议。国立教育学院副教授陈杰森(Jason Tan)则指出,转向非竞争心态之所以困难,在于教育既是公共品也是私人物品:政府强调社会流动与公平,家长自然聚焦为自己的孩子争取优势,“没有父母愿意多年后回头时后悔当初没有做得更多。”结构性不平等(社会网络与财务资源差距)也会强化竞赛,且大量“私人花钱”投入补习等项目,政府更难监管;对弱势家庭而言,教育常是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,因此“赌注更高”,家长的“用力”更像是对竞争体系的理性回应。
五、下一步改革可能走向何处?
受访家长普遍希望政府进一步检视重大考试,尤其是PSLE。51岁的梁安琪(Angela Leong)希望孩子能在多路径体系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,而不是过度依赖高风险考试来决定命运;她认为尽管体系不断变化,评估与成绩仍像阴影般存在,关键在于为每个孩子找到最契合其优势的道路。也有家长提出更温和的评估方式,例如引入更“切块式”的测验或项目,与标准化测试并行,在较不具威胁感的环境中评估孩子是否达到要求。黄女士则更直言希望出现PSLE替代方案,认为从幼儿园阶段开始的各类增益投入,最终都被导向同一场主要考试,这对年幼孩子造成“不必要的压力”。与此同时,家长也承认仍需要某种机制把学生分配到不同学校,问题在于如何降低单一关卡的决定性,并让多元路径真正同样被认可。
六、政治推动与社会阻力:教育改革的“烫手山芋”
在国会层面,要求改革的呼声持续存在。惹兰勿刹集选区议员符敦雅(Denise Phua)多年来致力于推动取消PSLE,并试点“直通车”制度(从小学直升到初中阶段);她认为替代方案“并非不可能”,但需先深入理解社会对PSLE的忧虑与可行的应对方式,再进行试点。她也指出仍需确保劳动力市场真正重视非学术技能与蓝领工作。其他议员也强调要在减压与备战未来之间取得平衡:有人认为学生需要更多机会在求学阶段探索兴趣与优势;也有人指出在生成式AI兴起、信息触手可及的时代,教师与学校需要更充足的支持与装备。反对党议员则表示将继续推动包括缩小班级规模等改革,并指出当AI开始复制部分白领工作,现行较“模板化”的路线可能不足以应对未来变化;但他们也承认体系迄今仍相当有效,因此推动根本性改革并不容易。
七、十字路口上的教育体系
政治观察者指出,教育政策之所以“难改”,正在于它牵动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:当体系仍被认为“相当有效”,彻底改造在一些人眼里反而显得“反直觉”;但压力与竞赛感又真实存在,使得教育改革长期处于“有人要变、有人抗拒”的拉扯。学者建议可从供给与结构面降低“追逐少数名校”的诱因,例如强化每所学校的特色课程与优势,让家长不必把选择收敛到少数“顶尖学校”;也有人提出在小一注册制度上提升公平性,让没有人脉与地缘优势的家庭获得更合理的机会。另有观点认为,PSLE并非全球通行的必备关卡,部分地区已取消类似考试或改采校本评估,显示制度设计存在不同可能性。但在现行体系的多个压力点中,学者也点名小一入学制度尤其突出:在一个强调择优的体系里,入学机会仍与家长能为申请过程带来什么高度相关,这种张力正是改革争议的核心之一。
更多信息请参阅:
编译自:新加坡海峡时报,2025-11-24
编译者: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沈华禹